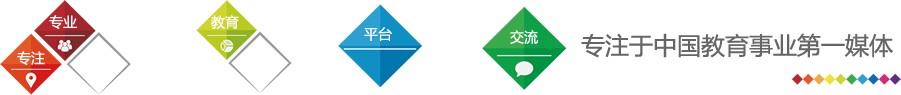【艺术简历】
关麟英蒙古族,1940年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1964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中国画专业。修业本科五年,师从吴镜汀、吴光宇、王雪涛、秦仲文、马晋、黄均等前辈。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研究员、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协会员、第八届全国美展评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文化大使、中国书画研究院名誉院长、内蒙古美术馆馆长。
作品《惠风和畅》参加由国际奥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第29届奥运会组委会共同组织的“2008奥林匹克美术大会”(OLYMPIC FINE ARTS 2008)(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作品同时被奥林匹克艺术中心荣誉收藏。
1990至1991年访问前苏联,1997年赴台湾进行文化交流。

《知己》 148×81cm
关于绘画艺术
绘画“移情”活动所依赖的客观外物的感性性质基本与艺术家主观心理需要相吻合。它们之间存在着诸多内在的关联。也就是说,主观心理心能频率与相应的客观外物生命运动形式的能量频率基本同步,形成共震而相互吸引。这时,“移情”活动才有可能展开。
在研究艺术家心理特征与艺术品风格特征的关系时发现,艺术风格的演变并非是因为艺术技巧的缺失和演变所致。艺术技法从严格的艺术品生成角度来看,它完全是从属于艺术家的心理需要。技法构建了艺术形式;艺术形成满足了艺术家心理需要。艺术心理的变化直接导致了艺术风格的演变。
如果人类的心理需要内在地转化为对艺术的追求。这种心理需要将通过艺术作品获得外在的显现;如果把这种心理需要投入到宗教领域,便体现在某种宗教活动中。艺术和宗教是同一心理状态在不同方面的客观表现。
艺术家把“自我”投入到一个其生命内涵与“自我”大致类同的外物中去玩味“自我”本身。这是“自我”心理需要客观化的自我审美愉悦。艺术现象本身即源于人们的心理需要。而在艺术活动中通过审美愉悦满足了这种心理需要。艺术品中的“自我”已不是现实中的“自我”,而是理想中的,自我观照的“自我”。使“自我”形式化、客观化。“当我们谈论艺术家所具有的、存在与这个艺术作品之中的艺术家观念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应当在这个艺术作品中找到这个艺术观念本身。与此相反,这个艺术家观念已经被投射在这个艺术作品之中了。它已经通过某些结构特色而客观化了。”(〔德〕莫里茨·盖格尔《艺术的意味》)

《春风得意》 136×68cm
精神的融入和物质的形式化,这个过程是艺术家展现“心灵”的绝佳时刻,完成了艺术品结构特征的塑造。艺术家在这个过程中突破了自身(自我)外壳的限制并超越了原本自我和物质外观表象的存在而使“灵光闪现”。对艺术品的观赏如果仅仅停留在对其色彩、形体等因素感兴趣而没有艺术家与观赏者之间的心灵感应,尽管这是一件好的艺术品,对观赏者来说,也就变得没什么意义了。
一切审美享受都是溯源于摆脱“自我”的本能。如果我们能够排除内在的矛盾将理念在艺术活动中自由地进入外物而使双重生命形式相互融合。“自我”就会体察到自由的愉悦。快感也始终是对自由的“自我”本能实现的感受。而不是出自于为满足简单的、机械式的对自然的模仿。此时,人们所关心的已不是外物的美在何处,而是判断此外物能否构成艺术品的资格。这种主客体相互融合的过程真实的满足了人们“自我”现实的心理本能。这一点,在人类心灵深处有着共同的体验。所有的“自我”都有共同的心理需要。这种共同的心理需要是跨地域、超越民族、种族,超出性别、宗教信仰和文化领域乃至政治体制和经济模式的“自我”认同。有着共同的存在价值.
艺术活动是“物”之“灵性”与“我”之“心性”相互交融的过程。中国画中的线条就非常清楚地蕴含了这种结合的存在。只要我们能够严格地按照线条本身所具有的形式感去认真地把握它。那么,在一副绘画作品中从线条最终呈现的式样来看,它已经具备了主客观两方面生命活动的跡象。它是主观心理特征与主宰外物生命内涵的高度集中、浓缩,形与神全在其中。这是主观心里对线条的限制、改造和充实的结果。这就使线条失去了本身的存在价值而成为人们的一种感受。
“移情”活动依然是通过外物去实现艺术家的心理需要。但是,这种由客体激发的“自我”实现仍然不能顺利地、没有障碍地去真正实现“自我”。因此,“移情”活动带来的心灵解脱只能是部分的、暂时的和不彻底的。而且还常常带有某种随意性,“移情”的深度决定着心灵慰藉的程度。

《春意浓》 68×68cm
“抽象”艺术心理活动源于人类对外部世界粉繁复杂、变化无常造成的不安和恐惧心理。“抽象”艺术品的作者没有对客观现实做理性的、深入的研究和思考,没有从理性的角度去控制由于不能安身立命的心理本能不安。这是由于他们对客观世界过于直觉把握而阻碍了他们的理性发展。摆脱不安和恐惧心理就成了“抽象”艺术活动的先决条件。故而可以看出,“抽象”艺术活动并不是理性介入的产物,也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是未受污染的心理本能。我们对一些抽象艺术品不了解、致使我们处于尴尬的境地,是因为我们没有抽象艺术家的心理因素。
在抽象艺术活动创造的艺术品中,看不到外部世界的影子。也找不到与外部世界有关联的种种生命迹象。作品的整体式样以及其中的每一个细节完全是超自然、超常识、超理性的对外部世界做直觉把握的心理本能的外在显现。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对空间的破坏和摧毁,使之摆脱外物对生命赖以生存的各种因素。在绝对的、永恒的形式中得以安身立命,使心灵获得解脱。这不是人类艺术行为的倒退,它是古代先民对严酷的外在现实表现得无能为力而产生的不安和恐惧心理的回归。
“抽象”艺术活动只是暂时摆脱了对尘世的感知。显露出缺乏恒常性和稳定性。这是由于艺术家的心理变化所致。“抽象”艺术活动只是在主观上破坏和摧毁外在空间的同时,又主观地制造了一个外在的形式——抽象艺术品,并在这主观制造的外在形式中感受某种安定感。实际上,这是从一个形式向另一个形式的转换。心理因素成为这个转换的动力。这个为满足心理变化需要而实施的形式转换十分坚实地变成一个念头转换之链,为永无止境的轮回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因。如果“抽象”艺术活动能称得上是“修心”的话,那么,这个“修心”行法则与外道修行和瑜伽修行所共有。它属于佛教修行的“世间道”。

《那达木》 136×68cm
艺术是较高层次的“修心养性”行法。这对大多数艺术家来说的确如此。但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阿莱克斯·葛瑞(美)(注)在《艺术的使命》一书中指出:“凡·高和罗斯克同样让人感觉奇怪的事情是:他们都创作了证实《神秘之光》存在的深奥的天才画作,也都死于自杀。这是为什么呢?”
阿莱克斯·葛瑞认为:“凡·高和罗斯克都缺少一个可以陪伴在他们身边的精神伴侣或一个热爱生活的配偶,随时留意他们情绪低落的危险时刻。两位艺术家缺少一位精神导师;缺少一个让他们产生归属感的团体;缺少对能阐释精神问题的传统做法的热情。因此,没有任何办法能在精神上帮助他们疏导穿越他们的创造力大潮……他们没有对自己本质属性和作为宇宙本质的无限仁慈的觉悟经历。”
凡·高和罗斯克的自杀,从佛教的观点去分析,“心”的问题要靠“修心”去解决,他们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心灵”的问题。艺术之路是“修心”的上乘之路,但也不是人人都能走得通。他们强烈的创作欲望使精神到了癫狂,走火入魔的地步。可惜,他们没有接触佛法的机会,不知道如何摆脱创作欲望“魔罗”的纠缠。他们认为自杀是最好的出路。像是神话中的“凤凰涅槃”, 企图在浴火中再生。但糟糕的是,自杀死亡,死后的路将更加难走。
(注)阿莱克斯·葛瑞(Alex Grey)美国当代著名的灵视艺术家和作家。也是一位大学教授和密宗修行者。“认知自由和伦理中心” 顾问。

《圣地春秋》 148×81cm
画家所表达的情感的一切特征都必须在艺术创造物——由艺术符号构成的“情感意象”中找到。“情感意象”应当是可以用笔墨清晰表达的东西。在艺术作品中除了艺术品整体式样所提供的情感因素之外,将看不到其它多余的东西。
中国传统绘画的所谓“骨法用笔”,是指原形物之“骨气” “风骨” “骨相”等。谢赫在“古画品录”里评曹不兴时说:“观其骨气名岂虚传。” 梁元帝在《古今书人优劣评》中指出:“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 “王僧虔书,纵复不端正,奕奕然有风流骨气。”“骨”就是原形物之“神韵”、即“生命内涵”。它可以是“刚”、也可以是“柔”。“骨法”当视为对原形物神韵进行抽取的活动与方式。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里提到“骨法用笔”时说:“凡画,气韵本于游心,神采生于用笔,用笔之难可识矣。”
在艺术实践中,线描的表情特征不是僵化的、固定不变的。比如做为中介的“圆润”“浑厚”“典雅”等,一旦注入画家不同的、独特的精神向往与感情追求,它的表情特征在程度上和在倾向性上便随之改变。人物画之“十八描”和山水里的各种皴法等技法在创作实践中亦然。
“骨法用笔”涉及到“笔力”的问题。“笔力”中的力,不是指握着笔的手在那里用力。“笔力”在中国画创作中与人体内的“气”有关。“气”和“血”是人体生命的两大支柱。“气血”旺,则身体健康,“气血”两亏,则生命危及。“笔力”是人体“气”携带能量的外用。
“心”通过“意念”去调控“气”,随着“意念”的指令去做“心”想做的事情。“意念”由“心”生,它是能量与信息的复合体。北京大学诸德莹教授在《中华传统养生的解读》一文中指出:“研究表明,人体的“气”具有一定的能量。通过“意念”的调控可能使分子构象发生改变。因而可能纠正不正常的分子构象。使生物的分子恢复正常功能。”(摘自《养生话语》张培林主编.华业出版社)。同样,我们也可以把“气”通过“意念”调控到“笔法”中去,使“气”和“笔法”融合。两者形成能量流——“内力”。通过“内力”将“意象”用“笔法”构建成为呈现外部存在的、有意味的艺术品有机形式。这个有机形式根据“意象”的特征由“意念”调控而诞生出轻、重、缓、急、干、湿、浓。淡等不同方向、变化多端的“笔法”,以便有效地施展为“心”服务的功能。“笔法”按照“意念”的指令使“意象”有机会完美地展现其自身。“万趣融其神似,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宗炳《画山水序》)。

《天高云淡》 68×68cm
艺术家创作意图与人体内的 “气轮”有关。“气轮”是分布在人体中轴线上由下至上的七个点。他是中脉上的主要点向四周放射出的支脉,形如车轮,故称之为脉轮。脉轮共有七轮。阿莱克斯·葛瑞(美) 在他的《艺术的使命》一书中提到:“ 最低一级的“气轮”也掌管着人的物欲和生存本能。如果艺术的动机只为低层次的物质利益和生存需要,那么此类艺术只能归于最低层。——外观和内容华而不实。为迎合流行或低级趣味而创作的艺术——或是集中于模仿别人的风格或主题。
第二级气轮是情感与性的交点。对应原始的表现主义和野兽派的快乐和激情、狂欢精神、污秽作品、传奇剧、诱使犯罪的主题和暴力情节以及失控的感觉。
第三级气轮与理性和智力有关。逻辑和策略在这类艺术品中表现出支配的地位。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蒙德里安和斯特拉有关的新颖作品。杜尚的讽刺幽默,波普艺术和欧普艺术作品的冷酷机智,极简抽象主义和概念艺术的简单枯燥。阿波罗式的平衡或克制。贯穿于第三气轮中的作品,无处不在。
与第四级气轮有关的作品把爱和激情作为首要的主题或动机。玛丽·卡萨特的作品表现了日常生活中的母子情。凯绥·珂勒惠支的绘画和版画表现了她对生活悲惨的普通人的爱和怜悯。戈雅的社会政治作品也是如此。苏·科(SUECOE)发自内心深处的油画和素描审问了当今世界的不公和苦难。
第五级气轮表现的是神圣的灵感和使命感,激发具有情感导向作用的作品。米开朗琪罗在《大卫》中捕获了这种神圣使命感,表现了无所畏惧的决心。格吕内瓦尔德的伊森海姆祭坛画中复活的基督,亚洲的菩萨雕塑和绘画也都是很好的表现宗教权威的例子。
第六级气轮即第三只眼。与杰出的预言家和光辉的神的原型形象有关。米开朗琪罗和布莱克的《最后的审判》既包含关于地狱和天堂的想象,也包括关于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想象。
第七级气轮(顶轮)代表的是瑜伽的目标。即于最高精神源泉(上帝)同在。——个人意志和神圣意志携手并肩,实现对精神领域的整体把握,并与宇宙合一。表现神圣融合状态的艺术品揭示了世界普遍联系的模式,或者指向无尽光明的宇宙。曼陀罗(轮形)是表现高级意识统一体的完美的创作手段……普贤菩萨和文殊菩萨分侍在赤裸初始佛普贤王如来左右两侧,合称释迦三尊或华严三圣。是西藏唐卡绘画终极圆满状态的一个象征。代表男性形象的深蓝色空间与代表女性创造力的白色能量的结合,象征着轮回(形式)和涅槃(虚无)的统一。令人心驰神往。

《草原健儿》 136×68cm
道教和禅宗的绘画向我们展示出一种把七级气轮能量融入艺术作品的成熟方法,这些艺术家的目标是冥想达到与对象合二为一的至高境界。”
外物神韵所展示生命运动的震动频率能否被人接受、认同。取决于人的心理特征发出的心理信息携带的能量震动频率是否与外物生命运动发出的能量震动频率同步、共震。一旦同步、共震,则相互吸引,相互融合。如此,才有可能完成“状物传情”的艺术使命。
审美价值不同于道德价值。道德价值只能体现人与社会的一定关系,而审美价值要广泛得多,它包括人类的创造精神和通过这种创造使人在物质和精神上在现实社会中获得确认。
体察到外物内在的生命活动特征以及自我心理活动与其结合的活动是实现“自我”的需要。这种需要有时显得特别强烈,甚至无法控制。当我们把“自我”移入到外物之后,“自我”也就在外物中获得了存在。从而使“自我”客观化。可以看出,人类对崇高的美的幢景都来自于摆脱原有“自我”而演变为非现实“自我”的心理本能。这种演变是人类对幸福的追求和感受的内心最深层面的最终本质。也是“艺术意志”的最终体现。当然,“艺术意志”只有在外界有机生命属于高级形态存在时才有实现的可能。同时也与我们自身生命活力需要展现所引起。最终使之成为使“艺术意志”客观化的审美自我享受。这种审美自我享受是在主客观相互作用下获得的。
“美”与“审美”不是同等的。“审美”标明组成美的一切东西。它组成了新的“审美”范畴和新的“审美”价值体系。现实中的“美”与“丑”都包括在这个范畴之内。如果我们把“丑”排斥在“审美”之外,那么我们也就相对地把“美”也排斥掉了。
谢赫在《古画品录》中评卫协、曹不兴、晋明帝、戴逵、丁光时等人的书法作品时提到的“壮气”、“神气”、“神韵”、“神韵气力”等内容就是指“意象”显视的精神力量,“作画时要心在画中之物”。“吾甚爱石涛”对花作画将人意,画笔传神总是春句。此是诗,亦是画理。(《黄宾虹画语录》)。
张彦远在《论画六法》里指出:“今之画纵得形似而气韵不生,以气韵求其画,则形似在其间矣”。张彦远所说的“气韵”包含了原形物之“生命运动形式”和画家主观审美意识。其作品的表现形式所显示的是某种生命运动节律以及它所显现的精神力量。笔墨使精神力量客观化了。

《春游图》 136×68cm
中国传统绘画重抒发而轻描写。故而色彩在中国画创作中则显得无关紧要,画家是根据“畅神”的需要去随意改变外物的颜色特征,又重新赋予原形物某种主观心理需要的色调,使其成为“情感意象”的组成部分。中国画在颜色运用上高度主观化了。例如“墨梅”“墨竹”“朱砂竹”“墨笔山水”“墨笔人物”等。“墨分五色”“光彩照眼”。墨色的“浑厚” “典雅”等是色彩所不及。
中国画在颜色的运用上一直讲“固有色”。所谓的“固有色”在自然界里是不存在的。颜色是自然外物外观表象的组成部分。但它是原形物外观表象之不稳定因素。它的不稳定来自于周围光线的变化。在阳光下,我们很难确定哪种绿色是树叶的“固有色”。因而,“固有色”只是人们主观的“假定色”,如果一味地强调“固有色”,这就会对画家精神自由展开带来束缚和障碍。非旦“不达画之理趣,”反而是“画蛇添足”
“经营位置”“搜尽奇峰打草稿”是画家构造“意象空间”(“胸中丘壑”)的活动过程。没有人能指出主客观融合而组成的“意象空间”是和哪个自然空间一模一样的。“意象空间”已经摆脱了主客观两者的自然存在状态而成为纯粹的、表达情感和生命特征的概念形式。它完全是独立存在的。
王微在《叙画》里说:“夫言绘画者,竟求容势而已。其古人之作画也,非以按城域。辩方州、标镇阜、划浸流。本乎形者融,灵而变动者心也。”“于是乎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以判躯之状,画寸眸之明”。
打破固有的视圈界限和时空概念的积极意义在于使画家从客体转到主体自身,从而取得了一个完整的主观境界。画家完全可以根据“畅神”的需要去安排画面,为自由“畅神”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和广阔的途径。画家所渴望的也正是在这样的境界中使生命自由展开。董崇惺说:“吾于画,不知所谓南宗北派也,当吾意而已。吾作山水树石,不知所谓阴阳向背,得物之天而已。当吾意,则不必悦世眼。得物之天,虽尺幅之内,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无害也。”
面对那些浑浊不清,变化无常的外物给人造成的视觉烦琐和心理不快,艺术家在艺术活动中对画面整体式样的经营,就是去掉那些令人感到烦琐和不快的东西。将外部世界有害的东西去掉了,才有可能有效地抓住有助于“畅神”的东西,并在艺术活动中体验“畅神”的愉悦。

《早春图》 178×88cm
艺术品应该成为各种复杂的审美感受和不同心理体验的“有意味的形式”。人类不同的个性价值不止从审美角度去体验,而且也应从心理本质特征的角度去把握,才可能是完整的。这里不存在价值关联的倾向。
“经营位置”是最为复杂的艺术活动过程。因而,谢赫把它称为“画之总要”。
“传移模写”的重点应着眼于原稿神韵流动、笔墨精妙处。且不必笔笔拘泥于原稿之形迹。要“仿古而有我”,笔笔从自家写出,又亦笔笔从古人得来。“会之有心”,必得古人笔法。要切忌不假思索,一味因袭古人,谨毛失貌的事。或不肯苦心多临,急于早立门户而导致轻浮浅薄、粗制滥造,这是造成作品不能别开生面的根由。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中国画的创新与发展。
“气韵生动”被谢赫列为“六法”之首。它是绘画作品给人总的感觉、总的印象。“六法”里其它五法的表现特质构成了画面的整体效果。在这个艺术整体中的每一个细节看上去都处于某种确定的相互关联之中。使人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把握其审美价值。
一件“气韵生动”的艺术品,它必然使人感觉到情感特征就直接存在于完美的形式中。在这个“表现性形式”里能够体察到艺术家人品、学识、才情、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内容。郭若虚在《论制作楷模》一文中指出:“大率图画风力气韵,固当在人”。在他的《论气韵非师》一文中提到:“人品即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即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所谓神之又神而能精焉”。
“气韵生动”必然是对构成艺术品整体式样深入探讨其构成因素的出发点和基础。其表现为对构成“气韵生动”的其他五法表现特质的美学研究。这有助于打破我们总是从模仿自然和单单从艺术品的内容为着眼点去研究艺术本身的问题。更主要的一点,是我们还必须从艺术品制造者个体主体心理特征去体察艺术品显示“气韵生动”的原因。而不是用我们自己或别人的审美观去评判艺术品的价值。更不能机械地套用某些有关信仰的抽象条文去审定艺术现象。艺术是属于艺术家个人的事。
艺术品之“气韵生动”是由艺术家“移情”冲动在艺术活动中“物”之“灵性”与“我”之“心性”完美结合、通过艺术家高超的艺术技法的巧妙运用所成就。因而,我们不能局限在平庸的状态去评判一件艺术品的审美价值;也不能用别的东西如外在的某种意识形态的需要去取代艺术家个体主体艺术意志。艺术家对人格的关照要胜过对艺术技法的注意。把人格视为艺术创作第一位的东西。这就需要真诚地注意对每个人的人格的尊重,才有可能对艺术现象和艺术品的尊重。

《早春》 66×66cm
人类形形色色的艺术心理源于外部形象世界的纷乱无常。世上有无以数计的艺术品、它们当中的每一件艺术品的审美价值都应该是独一无二的,不可等同。这就使得我们在评判艺术品审美价值时无法拿出一个划一的标准。这不可避免地给艺术品观赏和艺术品评论带来困难的挑战。
虽然对艺术品审美价值的评判没有划一的标准,但令人惊讶的是,大多数人对艺术品的观赏实际又离不开一个对艺术品的审美价值评判总的心理状态,即艺术创作似乎应以对外物精准、细微的描摹为其目的。像真的一样,则认为审美价值越高。亚瑟·叔本华在《心灵咒语》一书中指出:“大凡造型艺术作品,都是显示出这样一种分离,无论是油画还是雕塑,因而形式与物质的分离是美术作品的特点。对艺术品而言,弱化物质而将形式表现出来,是最为关键的。艺术品要非常明显以此为目的。由此我们也就知道为什么蜡制人形无法达到美学的效果。就美学意义上说也称不上是艺术品,尽管它们作工巧妙,甚至比优秀的绘画或雕塑更易让人产生幻象,足以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正因为此,这种看上去像僵尸一样的蜡像会令我们感到毛骨悚然”。
自然主义艺术与对自然纯粹模仿的不同点,用沃林格(原民主德国艺术史学家)的话说:“自然主义并不是要人们忠于其外表形态去表现客观对象,不是要人们抛弃对生命体的想象。自然主义是指唤醒对有机生命真实之美的感知,创作相应的对象。在自然主义艺术中人们所追求的并不是生活的真实,而是对有机生命的愉悦。”
至于说艺术可以陶冶人的情操,一般人是不会思考这方面的问题,就像不少佛教徒那样,他们根本不想了解佛学,不想弄清楚佛教是建立在怎样理论基础上的宗教,只知道求佛办私事。
在艺术品感情式样的塑造中,艺术技法直接与艺术家心理特征紧密地关联在一起。艺术技法是构成艺术品整体式样以及蕴含在这个整体式样中的艺术品审美价值的决定性条件之一,当一个缺乏艺术技法支撑的人急于求成地去进行艺术创作,他那些不成熟的艺术技法则很难有效地实现他的心理需要。成熟的艺术家都十分清楚艺术技法对创作有审美价值艺术品的意义。那些娴熟的技法可以帮助他们自如地“畅神”。 并在艺术活动中充分体现“畅神”的愉悦感。在他们平时的谈论中,提及最多的便是有关艺术技法方面的话题。
“用笔”是中国画创作实践中的一大难关.。想要突破这个难关,首先要弄明白”笔墨” 与“立意”的关系。任何艺术创作都必然是内容先行,表现技法紧跟。没有内容、没有技法,就不会有艺术品。

《巴彦布鲁克的人们》 136×68cm
“就一个艺术家而言,对技法的过分强调并不必然意味着他自己那些艺术作品缺乏更深刻的艺术价值。一旦整整一个时代的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技法的出色上,而不是集中在艺术价值上,那么,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某些艺术风格发展的开端,人们常常为了表现某种更深刻的艺术价值而在非常大的程度上忽视了艺术作品的内容,以至于尽管运用了技术手段,但却因为无视艺术作品的内容而使它们退化。晚期的哥德式艺术就沉湎于它那些艺术形式的精湛技巧之中,而晚期的巴洛克艺术则由于它那对透视画法和对弯曲多变的形体的特殊偏爱也偶尔会忘记,仅仅透视画法和那些变幻莫测的形体并不能构成一个艺术品。”(亚瑟·叔本华。《心灵咒语》)。
艺术的本质不是用以去克服人类遭遇的各种困难或去帮助实现某种利益需要,也与人通过耐力或聪明才智取得的各项成果无关。艺术不同于工业产品有模具、有标准件,更不像科学实验,不是科学发明。在艺术创作中、美学也无能为力为艺术创作提供准则。更不能具体指导艺术创作。美学能做的只是研究艺术家的创作过程以及研究艺术品观赏者的审美享受过程。例如,艺术品的审美差别;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之前所做的心理准备;艺术品所使用的材料特性对艺术家采用的技法以及感情投入等因素在艺术形式的结构上取得一致的作用。美学研究的对象还包括艺术家是如何关注所选择的审美对象等。由于美学不能直接参与艺术创作,这就给美学带来了局限和困难。
如何创作下一件艺术品,对艺术家来说,仍然是个未知数。
艺术不像说教那样把某个观念直截了当地表白出来。我们不能从艺术品中赤裸裸地看到艺术家的观点,虽然艺术家的观点已经通过艺术品的创作而将他的观点浸注在艺术品整体式样中给以客观化了。
在中国画创作中,我们会经常看到艺术家对“梅”“兰”“竹”“菊”等这些自然界的植物做不厌其烦、反复地关注和描写,原因在于这些植物的自然属性与生命特征和人类追求某些高尚情操的心理大致相符。他们便被称为“四君子”。艺术家之所以经久不衰地通过艺术形式去描写它们,是出于对“君子之德风”的仰慕心理,从而使这种仰慕的心理形式化,加之笔墨的运用,使之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如果艺术仅仅是给人们提供快乐和刺激,那么,现实生活中的游戏、旅游、甚至酗酒、赌博等同样可以给人们带来快乐和刺激,那些迎合人们日常生活中经验的和一般趣味性的作品,是对艺术的简单化、庸俗化。简单化、庸俗化的作品是不会有多少审美价值的。

《五月的风》136×68cm
在艺术家那里,爱情是神圣的、美好的,把它当作永恒的主题。“美”成了艺术品里的“积极价值”。而“色情”却被排斥在艺术品之外。尽管如此,“美”与“色情”之间却存在着天然的、内在的、微妙的关联。尤其在人类心理结构中,两者的关联最为密切。由于“美”与“色情”之间不存在等同,所以,“色情”的东西只有在它转换成能为“美”体现其魅力时它才具有”积极意义”。 “美”借助“色情”的支持和辅助获得了更加有效地展现自身魅力价值的机会。
艺术品具有的活力激发了潜藏于观赏艺术品的观赏者心灵深处长期被压抑的与艺术品具有的活力相同的活力。这个存在于观赏者自身的活力就获得了展现的机会,并在观赏艺术品时,从艺术品的整体式样中获得了貌似真实的审美体验,从中得到了心理满足。这时,艺术品的审美价值与观赏它的观赏者以双重生命形式存在,成为两者共同的东西。
艺术品审美价值把观赏者从现实生活琐碎的烦事中摆脱出来并获得心灵慰籍的能力可否实现,这取决于观赏者自身的生命存在状况。如果观赏艺术品的观赏者只凭借自身的生活经验在日常生活中按部就班、循规蹈距地度过生命的每一时刻,那他对艺术品审美价值的体验,只能是一种体验。艺术品的审美价值并没有成为他的价值观。他还是原来的他。那些经常对自己的生活状态反思的人,可能会更容易接受艺术品提供的审美价值。也更容易把艺术品中的艺术家观念成为自己的观念,虽然这种感染是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的。这时,艺术品提供的“积极价值”有利于激发观赏者内心的活力,有效地为自身生命流程提供帮助。这时,艺术品的功能才会真正发挥作用。完成了艺术控制人类心灵的使命。
艺术创作中的“用意”就是“用心”。“意”由“心”生。如果只是用“皴”“擦”“点”“染“等技法在纸上堆砌了几座山头就自认为是一幅山水画,这样的山水画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它无异于“补钠”, 即在纸上补布丁。在艺术创作中,艺术技法应一直跟着“心”去游动。一切都在“心”的掌控之中,绘画是用“心”去画,而不是单单用手去玩弄几种技法。要“心手相凑”, 而不是手在那里盲目孤行。
中国传统绘画在透视关系上主要采用“散点透视法”。这种透视法使画面呈现“鸟瞰”的效果。因而又称“鸟瞰法”。但画里面的人物、树木等又采用平视的方法,在一幅山水画里可以看到在重叠的山峦后面还有江河湖水以及帆影。远山用焦墨。在一幅画里出现多种透视法并没有使人产生视觉混乱。坐在家里的沙发上或躺在床上去欣赏一幅采用“散点透视法”创作的山水画,就如同穿越高山峻岭做一次长途跋涉的旅游,称之为“卧游”。

《高原春早》 68×68cm
目前人类的认识能力还无法找到宇宙的中心。而且宇宙中万物在不断的变化(死亡和新生,包括大小星系)人类可能永远也不可能完整地认识宇宙。因而,人类所谓的上、下、左、右、东、西、南、北等方向定位,只能说是人类方便生活的一种“臆想”。 在地球上也不存在“焦点透视法”中提到的“地平线”。地球是圆的,人类的视线不会拐弯,所以就在眼前的远处出了一条线,于是就把这条线称之为“地平线”。在人眼前的远处之所以出现所谓的“地平线”。也只不过是人类视觉的局限——,短视造成的错觉。如果你对着“焦点透视法”所谓的“地平线”往前走,那么,这条线也随之往前移动。你将永远也站不到“地平线”上。中国传统绘画打破了人类视觉的局限,在艺术创作中采用“散点透视法”。这种“鸟瞰式”的透视法既没有地平线之说,也不存在所谓地平线上的“焦点”,从而为艺术家“畅神”提供了无限的可能,使人回到了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原本状态。我就是宇宙,宇宙就是我。这是中国传统绘画创作最宝贵的遗产。
国画家根据“畅神”的需要,把不同地域、不同季节的自然物放在一幅画面里,从而打破了时空和地域的概念。如常见的《百花齐放图》《群芳吐艳图》《松鹤图》等。在《松鹤图》中画家把仙鹤(丹顶鹤)这种生活在草原湿地的鸟类安排在松树上。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丹顶鹤不会在树上筑巢。艺术家出于人类总是企盼长生不老的心理,把松、鹤同画一景,再加上一轮圆月,有延年益寿的美意。沈恬在他的文章中提到:“彦远评画,言王维画物,多不问四时,如画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莲花同画一景。“ 宗炳在《画山水序》里说:“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神之所畅,孰有先焉。” 这种心理需要只有在毫无障碍的(包括内在和外在的)时候,才能真正体味自由“畅神”的愉悦。这是中国传统绘画不同于西洋画的主要特点之一。这是“境由心造”观念之使然,一切都为“心”服务。

《初牧图》 136×68cm
自然界中之外物不一定都是具有诗情画意的。画家在艺术活动中对与其情感投合并能顺畅地移情其中的外物感兴趣;对那些与个人情感无关联、甚至有阻碍的物体感到不快。因而在“经营位置”时则采取了取舍的做法,对那些对表达情感无用的东西在构成画面时会无情的去掉。尽管这些令画家感到不舒服的物体在自然界里是与那些让画家感兴趣的物体是混杂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画家对那些感兴趣并能顺利畅神的物体给予突出、强化,使之能成为用笔墨清晰表达的东西。最后在画面里除了呈现画家心理需要的“情感意象”之外,将看不到其他多余的东西。在画面中除了“情感意象”之外还留有大大小小不同位置、不同形状的“空白”。(白纸)它们与“情感意象”共同组成了画面的整体式样。这些“空白”可以使“情感意象的实体”不受干扰地、充分地展示自身的存在价值。这些“空白”也同时成了艺术品“气韵生动”的重要因素。
中国画的传承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重要的组成部分。当今,有人坚持继承传统,也有人要彻底否定和抛弃中国传统绘画的一切,去另立炉灶。可这种人又说他们是画中国画的。亚瑟·叔本华在《心灵咒语》一书中指出:“历史对于人类就如同理性机能对于个人一样,也就是说,正是得益于人类的理性机能,人类才不会像动物那样仅仅局限于狭隘而又直观所见的现在,而在这个基础之上又认识到了大大扩张了的过去----它既与现在相联接,又是形成现在的理由所在。人类也只有经此种方式才可能真正明白现在本身,甚至将来。对于动物而言,由于牠们欠缺反省和回顾的能力,就只能局限于直观所见,即限于现在。所以,动物与人们在一起就是头脑简单的、浑噩的、无知的、无助的、听天由命的,即使驯服了的动物也是如此。与这种情形相类似的是一个民族不认识自己过去的历史,仅仅局限于目前这一代所知的现在,这样的民族,对于自己本身的现在所处的时代都不能正确理解,因为他们不能把现在与过去联系在一起,并利用过去来理解现在,于是他们也就更加无法预测未来。一个民族只有通过认识历史才能对自己的民族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献芝图》 80.2×53.5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