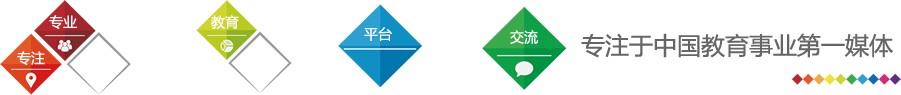由于长期跟踪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长江学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徐勇院长曾应邀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就此问题进行讲解。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每年都要为中央和地方决策部门提供大量调查咨询报告,因为调查及时、涉及领域广泛、针对性强,形成“三天一报,一周一批”的成效,即平均三天就要提供一份调查咨询报告,平均一周就会得到领导部门的批示,仅2015年,就有54份报告得到决策部门批示。
记者日前专访徐勇院长,请他与大家分享大学团队服务国家需求的经验和体会。
记者:文章合为时而著,您领导的学术团队关注现实问题,怎样理解其中的价值追求和学术旨趣?
徐勇:农村农民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政策目标、学术目标和历史目标是我们研究院三位一体的追求。
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长期将“顶天立地”作为理论研究的宗旨。所谓“顶天”,就是紧紧围绕解决农村农民问题的国家目标开展研究,将国家需要作为第一目的,我们团队将村民自治作为研究起点,并一直跟踪研究30多年。由于村民自治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多方面,30年来不同阶段其表现不同,我们的研究得以逐步扩展,并形成以村民自治和乡村治理为主要特色的研究机构。所谓“立地”,就是以实地田野调查作为基本方法,长期深入农村,进村入户实地调研,跟踪农村变迁,用调查得到的事实和数据服务于国家决策。实地调查不仅体现在研究之中,也贯彻在教学中,我们研究院的教学有两个课堂:校园和田园;两个老师:学者和农民。我们的学生平均每年在农村实地调查都在两个月以上。
作为学者,我们在调查基础上进行学术研究,以学术为本,间接为国家解决农村农民问题服务。我所在机构初创人张厚安在30多年前就明确提出我们的研究要“面向社会、面向农村、面向基层”和“理论务农”。
在实地调查中我们深深感到——许多昔日的村庄今天已成城镇,现代化是一个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国是世界上最为古老也最为发达的农业文明国家,留下丰富的历史财富,我们希望通过研究帮助在现代化进程中能够留得下“乡愁”,记得住“乡愁”。
记者:研究院30多年形成怎样的学术框架?
徐勇:我们在30多年的发展中,逐步形成了四大框架。其一是大调查,用事实说话。原来我们主要是围绕项目开展专项调查;自2006年开始,制定了“百村观察计划”,在全国选择300个村,5000个农户进行每年跟踪观察,至今连续进行10年,数千人参与,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2015年我们启动了“新版”农村调查,包括口述、家户、村庄、惯行、专题等,将普遍性调查与专门深度性调查结合起来。其二是大数据,用数据说话。为了掌握农村发展的规律,我们收集了大量的涉农数据,建立了大型的中国农村数据库,此外还收集了大量的涉农资料和文献。其三是大服务,说话要管用。我们与中央主管部门和涉农机构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及时了解中央和地方的决策需求,并有效地提供相应的报告。其四是大平台,让更多人说话。我们建立了全校、全省、全国乃至全球的协同关系,让更多人参与共同调查和研究。为保证调查质量,我们建立了专门的重点研究基地班,培养专门的调查人员。
记者:这些工作对推动改革、实践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徐勇:在学术研究方面,我们就推动农村改革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作出了特有贡献。比如,我们提出了“农民理性扩张”创造中国奇迹的观点,既解释了中国奇迹的创造主体问题,又预见中国奇迹将由于创造主体的变化而变化;以俄罗斯和印度的村社制为比较,提出中国传统底色是家户制,为中国农村发展道路寻找历史底色;提出产权单元与治理单元的均衡性,为中央1号文件关于乡村治理的思路提供了理论依据;我们就集体经济与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作出了大量理论探讨。
在历史传承方面,我们收集整理了大量农村资料,出版了《最后的农民》《消逝的村庄》等画册,拍摄了数十部记录农村历史的专题视频,记录了数千农民的口述。
记者:请您就今后的计划进行展望。
徐勇:中国正在成为崛起的大国,崛起的大国应该有与其相匹配的学术文化工程。这种历史使命感促使我们将要在大调查基础上,建设全球顶级的农村调查机构。在世界农村调查历史上,18世纪前看英国,19世纪看俄国,20世纪看日本,21世纪要看中国。除了每年出版的《中国农村调查》以外,我们正在翻译和出版日本《满铁农村调查》《俄国农村调查》《英国农村调查》《法国农村调查》《德国农村调查》《非洲农村调查》等。国家现在推行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我相信,经过不懈努力,我们能够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农村调查机构的目标!
《 人民日报 》( 2016年02月18日 1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