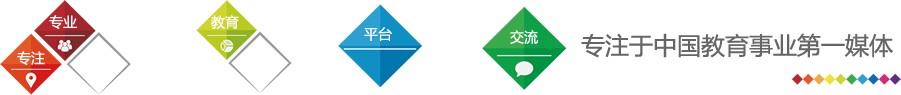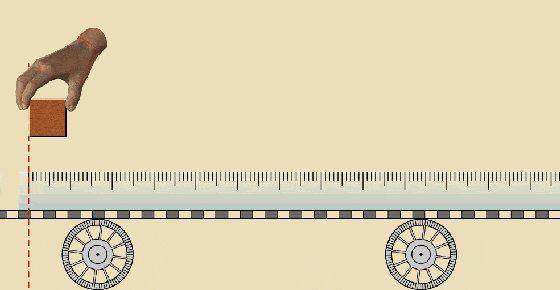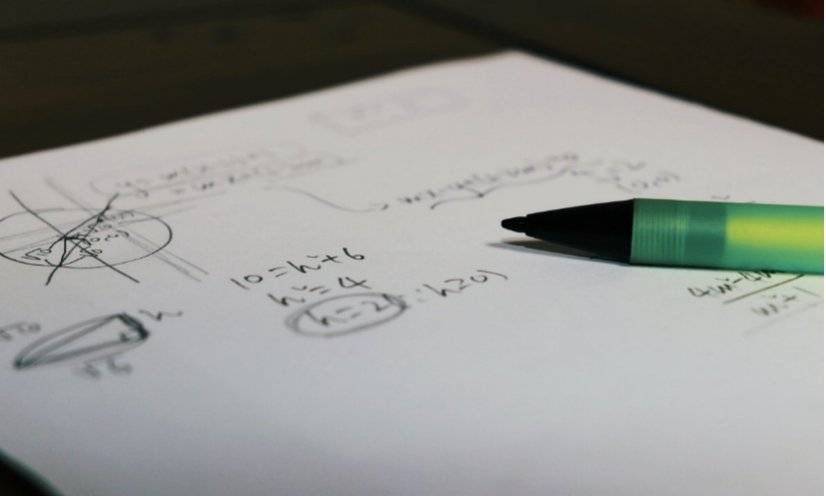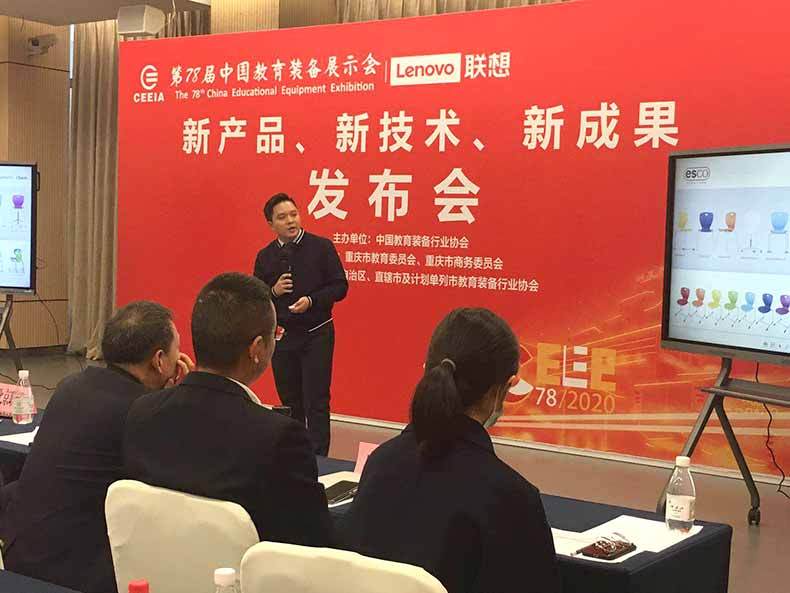近日,由作家、记者、文学批评家郎生独立完成的中国古典文学史著《补白——中国文言小说的传统与辉煌》,由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该著从文学内部,对中国宋前的文言小说,进行了视野广阔而又言之有据的点评和论述,使之与众多由历史角度书写的中国文言小说史著区别开来。如对原作的直接解读,对先唐文言小说传统的首次发现,及对倍受轻忽的唐五代传奇之辉煌、超前成就的全新论评,为中国古典文学史的研究和著述,补了一个白。评述之时,还与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宋元后的文言小说和西方现当代小说做了比较,探讨其异同及关联。被评者誉为“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后,又一部真正新颖独到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著、文学论著。”
郎生来自藏语,起这样的笔名,当与其经历和自我评价有关。坦率说来,我一生从文,同道好友者无几,郎生其一。不因别的,是我们共同的文命,即我们都竭尽全力做自己的文字,也都不惜心血,可辛苦此生,文命两舛。我居京,出书路子比他多一些,混得稍强些,但曾经也不过是文字糊口的人生而已。
认识郎生,是十多年前,开始时不怎么了解。但后来往来中的一件件事实,让我与他之间的情义,愈加铁磁。读他第一部作品,是自传体长篇《拉萨的月亮》(再版更名为《雪域历》),感觉好极。之后,是他的《转世秘藏》,一部至今未能出版的后现代短篇集,读后佩服得五体投地。每隔几年,他总会有一部新的随笔写出来,尽管还总是出版不了,但感觉仍是惊人的好。自此在我内心,便认定了他的写作。我私以为,一个写作者,和工匠师傅有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活儿做到了一定程度,便知道文名的大小与活路的好歹,实在是不相干的两件事情。我大概也是通过《骚土》数十年的磨练,才稍稍弄懂了这个道理。
郎生也是,他发现和推举的昆明少年天才杨墨、云南巧家作家孙世祥等,都是生前默默无闻,去世后轰动一时的人物。所以像郎生这样的写作者,在今天这样的处境,我虽偶尔会笑上天的不公,但也知道,这实在怪不得老天,都是个人癖性的使然。是的,是他们这种人不愿意趋炎附势,此为其一。其二更为真实也更为无奈的恐怕是,他们更愿意孤独,所以才选择了一个人隐蔽的生活与写作。他们似乎天然地顺从一个道理,即一个写作者,想写出富有灵性和尊严的精神性文字,少一分个人的自由,似乎都不大可能。
这就构成了他们特殊的文命。不过这样也好,这能使他们安下心来,老老实实地投入到写作里头,一心一意的雕琢文字,给这个世界留下点真正经得起推敲的作品。所以说对于时代,也有该感谢它的地方,那便是正是因为它的遮蔽和扭曲,反而能制造出个别顶尖级的、癖性殊异的人物。看到郎生发来的书稿,看到这本书中他许多独到的发现和许多闪光的认识亮点,顿觉其视野宏阔、举重若轻、文理恣肆。
我知道,这一两年间,郎生往常的写作似乎停了下来,一门心思钻进先唐述异和唐代传奇里头,以一个深谙写作之道者的刁钻眼光,去阅读感受,去发微探幽,下死功夫去摆弄这门看似古怪冷僻的学问。虽然我与他时而也会在电话里讨论几句,但我自知,以我对古文学的浅尝辄止,跟他已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了。

这本书的起源,最初是郎生每日在朋友圈中所发的微信,一段一段的,自然地出现在手机里。那些日子,我时常就将它们当作即时的休闲,一边欣赏他抒发的风趣,一边又吃惊于他见识的独到。我们时而也通通电话,他在电话里说先秦、道汉唐,无论魏晋,有时候像是他自己一个人在喃喃自语,又像是在与远古的写作者们直接对谈。另一端的我答不上话,却也能感觉到他的痴迷是如此之深。我电话这边打哈哈说,原来古人才是写微信的高手啊。譬如,在这本书提到的汉代小说《神异经》里,就有这样的段子:
东荒山中有大石室,东王公居焉。长一丈,头发皓白,人形鸟面而虎尾,载一黑熊,左右顾望。恒与一玉女投壶,每投千二百矫,设有入不出者,天为之医嘘;矫出脱误不接者,天为之笑。
东方有人焉,男皆朱衣缟带元冠,女皆采衣,男女便转可爱,恒恭坐而不相犯,相誉而不相毁。见人有患,投死救之。名曰善人。一名敬,一名美,不妄言,果果然而笑,仓促见之如痴。
无论是住在大石室内、骑着黑熊、人形鸟面而虎尾的东王公,还是那些只会憨笑、互不相犯又能以死相救的东方人,都会让你产生无尽的联想,吃惊于我们老祖先所写的段子,真是妙不可言。
早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时我的《骚土》还未动笔,只是满世界地搜罗各种奇思异想。读到两晋志怪或者是唐代传奇的一些章节,便隐隐约约地觉得,这是躲不过去的一个功课。但那时文学界的写作者,正是人人目光向外,为各种外来炫目的技巧所感染,都在求新求异的档口。我几乎也挟裹其中,对郎生今天所做的这门看似偏冷的学问,只是浮皮掠过,没有像他今天这般的深入。
只是到后来,阅读到明清笔记的时候,才半悟不悟地理解到了,中国小说的叙述方式,似乎古来就存在一条看不见的隐线,它是沿着这条看不见的隐线行进发展过来的。这个我想,百年来,鲁迅、钱钟书、沈从文、汪曾祺等,作家中极个别最优秀的写作者们,大概也都是知道的。我的写作,如果当时没有感觉到这条隐线的存在,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骚土》。
我觉得郎生的这本书,给我们了解先唐及唐代小说天才作家们的面貌,提供了一个生动形象的版本;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后,又一部真正新颖独到的中国小说史著、文学论著。对多元化、国际化的唐代文学来说,也只有贯通中西的郎生才有体悟。读到这里,我确乎才意识到了,历史里的那些志怪和传奇,无论写作者是多么的显赫或者一文不名,但在我们的文学纪史中,大多仍是隐蔽着的影子,与其时文坛上的炎炎盛名者不是一回事情。而后来被我们津津乐道的许多作品,也多是这类隐蔽写作的结果。
此时我居然才知晓,我们最早的故事、小说,作为人类的叙述智慧之一,是从源头开始便独立了出来的。之后一批又一批的写作者,前赴后继,代不乏人。他们深藏着我们文字血脉中的DNA,也就是我们文学传统的内核,也就是文学本身演进的历史,给我们认识世界、认识人类自身的真伪,提供了真切无比的判断方式和标准。文学与政治、宗教,与经史等其它文化样式,是平等甚而是竞争的关系,且一直在雄心勃勃地独立发展,构造着一个隐蔽的文学王国。是我们民族中这些锦胸绣口的天才,通过一代代人不断线的努力,才有了唐宋文学堂皇的面貌,才有了中国小说潜流至明清的正脉。这条文学历史隐线的发现,我想对于今后的中国文学,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一个具有艺术野心的作家,应该了解自己在写作中默默踏上的这条历史线索意味着什么,因为这样的文学无论时潮如何地忽视和遮蔽,最终仍将会成为传统的代表和主流。
所以,简而言之,我以为此书大概也将是一个好作家的案头必读。至于活跃在当今文坛那些对这条文学隐线或这种文学传统不管不顾,仍洋洋自得于一己聪明的写作者,我只能对他们的自信和勇敢表示敬意。至于其作品未来的价值,几乎是不用怀疑的渺茫。当然,或许他们之中的个别人,确因天地氤氲、情动于衷,有可能写出一两个灵动的文本,但是,没有这片隐蔽的深厚沃土的滋养,也只能算是漂亮的风筝。
郎生通过这本书告诉我们:其实,一个时代最深刻、最神奇、最壮美的形象,不是自然景观,不是炫目五色,也不是眼见耳闻的过往,而是我们胸口里头这颗和古人一样的跳动的内心,以及这颗心对世界用文学构造的意象。这便是这条隐线的价值。还有,正如郎生所揭示的那样,文学尤其小说,从古至今最重要的功用之一无非就是娱乐,在没有意义的人生中寻找并创造着不一样的意味和乐趣。是时候恢复它的本来面目了。(文/老村)